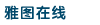一个小时后,我走了。
回到家,妻迷迷糊糊地问我去哪里了。
我说明天提案的资料忘在公司里。
妻恩了一声,把脑袋蹭在我怀里又睡了。
这个理由差到极点。
我决定不再找女儿了,也就没力气编更好的理由了。
第二天下班回到家,桌子上有一张纸上写。
不要来找我。
我怔怔地站在当地。
真觉得在做梦。
噩梦总是连着一个噩梦,永远做不醒一样。
天渐渐黑了。
终于有人敲门,我冲过去开。
是女儿。
那时我失去理智,拽住她喊。
你跟她说了什么!
她只是怔怔望着我说。
孩子失踪了。
她从口袋里掏出张照片。
那是相册中的一张,是三年前拍的。
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到。
她的背后,有一面镜子。
镜子里那个人是我。那个晚上我们通宵都没有睡,我们坐在彼此熟悉的环境里。
因为少了一个人,我们变得如此陌生。
近半年以来,我与她的关系是得以妻的存在而赖以维持的,而妻一旦走开,所有的维系在刹那间便呈现出其狰狞的本质。
有时候你认为是阻碍的东西,等到撤消,你才发现是唯一的维系。
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。
我们根本不敢对视。于是我们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寻找妻的下落。
我们寻访各种我们认识的人。
我们拨打无数个我这辈子都不会拨的电话。
在这种类似同舟共济的努力上,我们暂时忘却我们的罪恶。
无论如何,当你用尽全力去赎罪,去弥补的时候,感觉是会好一些的。
尽管你深知,这种努力完全徒劳。 所以每到晚上,共对的时候。
我们就特别地沉默。 四月初的时候,我们收到了妻的信。
严格说来,那不是一封信,是一张信封,和里面的两张船票。
我记得那天下午,我打开信箱,看到熟悉的笔迹。 心跳几乎停止。
在拆信的当时,手都在发抖,害怕跌落出一张遗体鉴定书。
竟然是两张船票。 我把船票交给女儿的时候,她也呆住了。
这是三天后的船。
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,没有到了那之后如何,没有具体的提示,没有多余一个字,就是光洁的两张船票。
妻料到我们势在必行。
我们的确势在必行。 我们剩下三天。
前途完全未卜。
妻为什么剩三天给我们呢?是让我们准备行李吗?
还是准备后事?
我去公司,召集部门主管开会。
说离开一段时间。
我把工作调配得井然有序,把接下去的工作计划全部排好。
警告小辈在我不在时不许偷懒。
私交好的同事暗地问我,究竟要出行几天,我摇头。 女儿显得很奇怪,她在这三天里选择买衣服。
相对于我,她似乎过节一样。
让我无论如何抽出一天来,陪她买衣服。 我们一家家店逛,她拉着我的手兴高采烈地流连在不同的商铺里。
享受和每一个老板侃价的乐趣。
买了一堆五颜六色的大包小包,又嚷着肚子饿,拽我去餐厅吃饭。
吸着绿色的果汁,两眼朝我骨溜溜地转。
随即笑起来,吸起半吸管,朝着我慢慢吐出来。 有时我真怀疑我和她不是将要去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地方,而是压根就在夏威夷度假。 在起程前的最后一晚,我们做爱了。
这是我们重遇后到那天第一次做爱。 我记得那是从外面购物完回来,我们都在各自默默整理自己的行李。
出差过无数次,第一次不知道往自己的箱子里放什么。
她更加绝,买的衣服,没有一件放进箱子。
我们就这么互相不说话地,各自理自己的衣服。
我不知道她究竟在箱子里放了什么,整个行李箱都合不上,她就跳上去,坐得非常开心。 后来才知道,她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,沙发靠垫,地毯,尽量在拖延整理的时间。
因为我们都知道,理完后相对的场面是致命的。 但终究这场面还是到来了。
她终于把箱子合上了。
我和她互相望着。 我们终于慢慢走近,同时伸出手臂抱住对方。
用嘴唇寻找彼此。
从到到尾我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用极其缓慢的动作脱着彼此的衣服,好象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。 记忆中,那晚她的叫声是最为凄楚的。 第二天,我们一前一后,提着箱子上了船。
妻的卡里有不少钱,她似乎也极大方地给我们买了两张头等舱的船票。
船是豪华邮轮。
具体开往什么地方,由于和这个故事本身关系不大,我就不多说了。
总之,我与女儿登上船的刹那,我感觉象登上泰坦尼克一般。
撞上冰块,然后一起沉没,然后手拉手一起葬身。
我那时还不知道,虽然这看起来很悲惨,但相比与今后实在发生的事,那样要幸福和美丽得多了。
船启程的时候,是傍晚。
我和她站在栏杆处,望着下面翻滚的江水。
冷吧?我看看她。
还好,她朝我羞涩地看了一眼,转身进了房间。 自从昨夜那一场看似突如其来却势在必行的做爱后,我们就很难正常地说话。
这对我们来说,象一个各自必须珍藏,却永远不能放在我们中间,供我们正视的事情。
我盯着船离岸越来越远。 岸边送行的人渐渐散去,有一个人还在那里怔怔地望着我们。
那个人是妻。
我和她逐渐地对视着,视线逐渐拉远,我想叫出声喊,但嗓子居然是哑的。
我不知道这船的离开,这妻的站立,是什么意思。
女儿当时在船舱里。
我怔怔地望着妻,妻远远地,面无表情地看着我,举手朝我挥别。 这个场面,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,非常非常的恐怖。
我们渐渐地开远了。
妻变成一个再也望不见的点。
海上只有一些浮标,随着海浪逐渐漂浮,我脸色惨白,象被冰雹砸了五个小时一样,回到船舱,看着女儿。 怎么啦?她抬头问我。
没有什么。我勉强笑笑。
她噢了一声,站起来不看我,我吃饭去了,就蹦蹦跳跳地开了门,去了餐厅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告诉她刚才的景象,可能是怕她承受不住,可能事情本身已经超出了我能预计的范围,我感觉到船以某种稳定的振幅前进着。 船舱里的喇叭居然会放音乐。
我坐在船舱的床上安静地听着音乐,回忆着妻刚才的眼神,准确说来,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眼神,或许,只有在彼此逐渐消失在视线的最后刹那,我从中读到了些许不舍的东西,但那也很有可能是我的一相情愿。 到了晚上10点多,女儿回来了,她已然喝醉。
我们去跳舞吧。她一把牵住我手,把我往外拖。
我使劲摔开她手,看着她。
你看我干吗?她冲着我喊,你看着我干吗?
我其实心里非常明白,女儿对目的地,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百万个可能充满恐惧,在这种恐惧之下她选择了一种疯狂的发泄,无论是买衣服,还是跳舞,都是她对此的反抗。
我不能告诉女儿此行已然毫无意义,生活当中随时会有某种旋涡状的东西,我已感受到它的存在,可我只能咬住牙关,不便透露,因为这无比险恶。 我安静地看着她。
她突然笑了,你早点睡,我去玩了。
她在我面前脱下衣服,换了一件无比性感的衣服,打开门头也不回地出去。
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。
到开门去了轮船的酒吧,推进门就看见一个长发的女子以无比专业的舞蹈震慑着所有人,赢来所有的掌声。
每一个男人的眼神都是垂涎欲滴的。
真是帮猪。
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舞蹈,或许我对此本身就不熟悉,它非常的性感,但这种性感因为某种专业性在里面,故而增添了一种凛然自威的东西在里面。
N年前,她已是DANCING QUEEN。
我找了吧台处坐下。
她一曲跳完,走到吧台处,不看我,自然有男人上来请她喝酒了。
于是他们就在我边上。
接下去是对话。
小姐,可以认识一下吗
小姐,喝杯酒如何?
小姐,你是一个人吗?
小姐,你是学舞蹈的?
就搭讪的言语的贫乏与庸俗性而言,这个男人实在无药可救。
女儿低头笑笑,不说话,那男人更加着迷。
围着女儿忙得团团转,小姐,可以请你跳支舞吗?
女儿笑得非常文雅,好象小家碧玉。
多年前,她就会笑得象只小狐狸了。我不忍再看下去,一个人拿了杯子欲走。
刚要走时,突然听到她说。
不行,我要和这位先生跳。
突然好几个人眼光转向我。
我回敬他们。
女儿走上来,仰头望着我的眼睛,先生,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? 我微笑,不答。
她继续问,先生,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?
我微笑,不答。
她执拗地,先生,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?
音乐已经响到一半,只有她一个人在对着我问。
她的眼眶里已经有东西在闪。
还在苦苦追问,先生,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?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