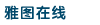|
魏玛共和国亡时,知识圈一度流传这样的段子:古时有刀法极好的刽子手,一日有犯人受刑,刀光闪过,犯人疑惑:“我的头不是还在么?”那刽子手说:“你低头试试看。”这个可怜的犯人,自然是被拿来比作魏玛。这段彼得·盖伊写在《魏玛传奇》里的旧事,更像是一针历史的杜冷丁:把一个邪恶的天才钉在罪恶的十字架上,换来沉默的大多数躲避在受害者的棚屋里。奥地利导演哈内克的电影《白丝带》会激起激烈的反弹,原因也大抵在此——他把“受害者”拉出庇护所,然后说:“那罪恶里,也有你们的一份。” 电影始于回忆——1914年的童年,德国的偏远山村,“它们也许和20年后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有关。”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,20年后,德国6500万民众选出来的元首,带来一场席卷欧洲的浩劫。因这背景,《白丝带》很容易被看作是对那段黑暗往事的解释,但哈内克的野心也许更大。 借着乡村教师的一双眼,我们打量起《白丝带》里这座村落:农舍一丝不苟,村民彬彬有礼,唱诗班的童声在寂静的空气里悬浮……而这克制安谧之下,隐秘的恶意渗透在空气里,孩子们的童真亦已败坏,在平静的遮羞布下,是一个被暴力撕扯的小世界。消色处理后凌厉的黑白画面,如下探的钻头,刺探人性的黑暗区间,一路朝下,触到了最坚硬的内核,权力。在那个看似井井有条的村落里,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以权力标记:妻子服从丈夫,孩子服从父母,村民服从男爵,教徒服从神父。那个世界的法则是权力,并最终被滥用的权力腐蚀了。这是酿成第三帝国的悲剧原因,也是像奥威尔曾经形容的:这个世界悲剧的根源在于权力的被滥用。 如果只是触及“权力”这个命题本身,《白丝带》还不至让人那么不安。阿伦特在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里提及的“平庸的罪”,在哈内克的影像里回旋。在阿伦特形容的那个“集体处于无可救药的迷茫状态”的年代里,那些“受罚”的人,他们放弃了思考和清醒的努力,他们没有权力,但是他们选择了顺从权力,并且将有一日,他们会把自己曾经承受的,施加给更弱的人。孩子们在村里的恶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,这群孩子在成年后,将选择依附更强大的权力,并随之向周遭的世界施加更恶劣的暴力。我们或许可以寻找诸如通货膨胀或者革命挫败等宏大的原因来解释1920年代末德国社会的动荡和转折,但更残酷的事实在于,在《白丝带》里现形的幽灵,不是只出现在彼时的德国。而这,才是哈内克强迫我们面对的最大压力。 于是,这注定不是一部让人心安的电影。“白丝带”在电影里的第一次出现,是在神父体罚了一双儿女之后,纯白的丝带是纯洁,也是耻辱,这让人不寒而栗的“优美”画面,成了这电影的一帧定格:多少暴虐,以圣洁为名。 来源: 文汇报
|